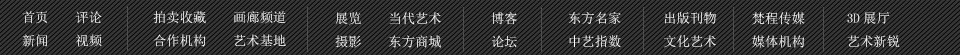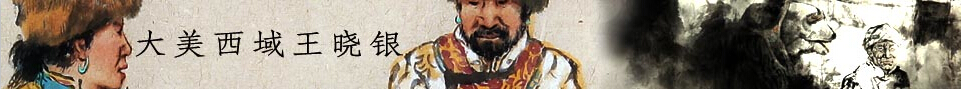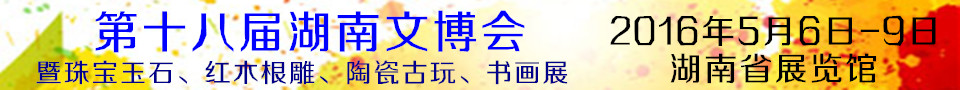|
1989年2月,中国现代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混乱而充满活力的展览在箫鲁发出的两枪之后,为八十年代艺术史划下了句号。6月,何森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像之前大多数的毕业生一样,在国家的分配与安排下,他被指定到重庆第四十中学校当美术老师。这是一个记忆和理解力对年轻人的一生起关键作用的时期,二十一岁的毕业生对之前发生在学校以及成都、昆明等城市的现代艺术活动已经有充分的了解。他回忆说在还没有考上美院的时候就经常去四川美院,目的是想了解充满刺激的信息,观看那些他已经熟知的艺术家的作品。“为什么我要考四川美术学院,因为77级、78级出了很多全国非常有影响的艺术家,罗中立、程丛林、何多苓,周春芽,张晓刚等让我们特别的敬仰。”对于像何森这样年轻画家的来说,这个背景几乎是决定性的,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发生于1979年的伤痕绘画、八十年代中期的西南现代艺术活动(成都的“红黄蓝”团体、昆明的“新具像”团体以及之后的西南艺术群体的不同活动与展览),生活并工作在重庆和成都的年轻画家会是怎样的结果。张晓刚是何森的老师,作为八五时期西南地区的表现主义艺术家,张对学生的影响是直接的,他鼓励学生自由的创作和举办展览。就像重庆特殊的气候与美术学院具体的环境所构成的空气一样,从70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发生在四川和西南地区的现代艺术充满复杂性:对历史的反思开始于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例如高小华、程丛林、罗中立;对艺术的真实性的直接感受来自敏感的周春芽、张晓刚、叶永青;对人的内心的孤独的理解来自阅读萨特、索尔贝娄、郝塞的毛旭辉。他们之间不是同学就是朋友,他们因对艺术自由的理解而成为保持不断联系的战友。对于那些渴望理解新艺术的人来说,他们构成了实质性的、摆脱不掉的精神资源。 直至1988年,改革的空气已经浸染了大街小巷几乎十年的时间,没有任何时候像1988年那样充满动荡与可能性。急促的经济增长和缓慢的改革体制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几年的市场经济机制的发展,更进一步打乱了由过去所确立的社会运转秩序。伴随改革而来的种种令人不安的现象开始涌现:数以千万计的农村人口抛弃农业生产流入他们渴望的大城市;部分工厂的倒闭、开工不足以及在不久的时间之内很可能产生千百万失业大军的说法让人恐慌;交通铁路方面因为管理不善不断发生恶性事件;大学校园里弥漫着种种荒诞、冷漠、肤浅、颓废、慌乱的精神状态;加之通货膨胀,“官倒”盛行,官员腐败,这一切,在人们心中构成了难以承受的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艺术家开始关注个人,关注细小的变化带来的问题。直至1989年5月,社会与政治的冲突达到沸点时,灵魂的反映变得更为复杂起来。 何森的毕业创作呈现出视觉习惯上的厚重特征,他在他的《残缺世界的注解》里保留了空间的深度与诡异。显然,超现实主义的观念影响了这位毕业生,但是,在气质上,这种诡异与之前的伤痕绘画例如程丛林从《近卫军行刑的早晨》吸收而来的晦涩、表现主义绘画例如张晓刚的《病床》里的恐惧有些相似。这种影响肯定是潜移默化而不经意的,但却是自然而然的。八五运动提供了所有现代主义资源,只要愿意,任何年轻人都可以借用。毕业创作完成于1989年4、5月期间,这正是动乱而导致人们心神不定的时刻,可是,对个人状态与问题的敏感和关注,使得画家将心神不定的状态控制在一个冷漠与让人疲倦的环境中。画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他假设的场景,一个也许与自己的生活环境和习惯非常接近的空间,这个空间出现在“纸”上,这表明画家不太愿意将这个空间视为真实的现实,空间被认定为一种假设。这个时期(直至1991年),同样对“纸”的效果充满兴趣的同学还有沈小彤,对类似超现实的环境给予表现的有郭伟。这当然是一个心理矛盾,这是对自己生存的环境的质疑。在离开学校进入社会之后,何森沿着这样的感受完成了很多作品:在《静物和人》(1990年)这类作品里,何森将自己使用或者熟悉的生活用品放进了构图里,书包、衣物、杯子、烟灰缸以及长短不齐的烟头。这些东西象征着刚刚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后个人生活的混乱,事实上,它们的存在成为画家关注个人生活而脱离85时期本质主义追问的证据。直至1991年底,何森将自己身边的朋友和同学作为表现的对象,与伤痕传统不同的是,这些人不再围绕一个目的和问题的中心,他们虽然被画家安排在一个构图中,但是,他们的表情和动态之间没有联系(《椅上的两人》、《愉快的年华》1991年)。这就是说,本质主义的心理情节受到忽略,尽管画家用复杂的笔触保留着老师们给予的“深度”追忆的痕迹——一种难以很快割舍的眷念。究竟是感觉唤起了新的意识,还是新生代绘画产生了影响,无论如何,何森这个时候对现实的感受与北京的画家一定有相似之处,何森在1996年对《画廊》编辑说: 1991年到1992年间我的那批作品基本上是这之前个人经验、文化积累与多年某种莫名冲动的总和。它给画面中那些熟人、朋友和私人用品赋予神圣的意义,而作为个人偏好的表现主义语言自然成为代言人。这批作品中将私人性无限放大的“近距离”特点恰好与当时北京“新生代”画家的处理方式相契合,以致在“后’89”展览中被归入“泼皮”类。但我认为作品中具有的英雄主义气氛和表现主义语汇是同“玩世”态度是相悖的,但作品中除了个人情绪的排解与渲泄外,缺乏更为宽泛的社会含义,于是在1993年我作了仅限于题材转换的调整,如表现社会场景的游行和象征意味的铜鸟。 (责任编辑:卓艺梵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