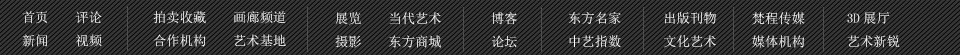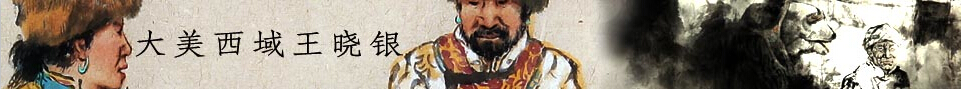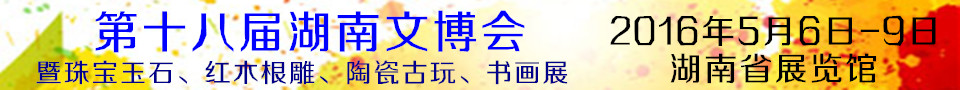|
潘钺是我在中央美院的同届校友,印象中他沉默寡言、性情平和,一说话偶尔会露出些善意的小小“坏笑”的一个同学。 他的油画作品我看过一些,很工整很严谨很内敛,一如他沉默的外表后有些不可捉摸的内心,但你却是分明能够感受到其中狷介不阿、且颇有些孤傲的成分,这种印象一直持续到我多年后再次见到他——他依然如故。 有时人和人相遇的机缘是很不可思议的,作为校友,我不算很熟识他,这么多年过去,我们已将人生的很多滋味经历过,也算有些阅历了,除了外貌神气上都会多几分沧桑,我不知他会有怎样的改变,再见他时,是为他的摄影作品写写文字,也因此,由他的作品让我发现了很多以往没有可能感受到的东西。 “我拍的这些人物存在于中国现实的北方农村,有以唱戏为生的县级演员、有过年跳秧歌的普通农民……我是自驾车辆,装着大幅机箱、外拍灯和灯架、速装背景纸、重型三脚架、借用当地农民的住房来完成这些片子的。这是一套影楼影棚的拍摄工具,我用它来拍摄最不可能走进这个环境的现实群体,他们脸上的被记录下来的内容和这种获取影像的方式本身就格格不入……最起码我觉得我还在关注中国目前的一些弱势或边缘群体,我想让人们看清楚他们脸上的不同于美女帅哥的痕迹,他们绝对是当代的最真实的一部分面孔:传统和现实、喜庆与麻木、华丽与空洞……很多东西交织在一起!他们虽然也化装,但那不是修饰和遮盖,那是一种强调和提纯。” 对的,“强调和提纯”恰恰也是他的摄影作品予人的最深切的印象和感受。油画家的大“转型”,先例不在少数,但我们看到更多的艺术家是放弃以往为大家所熟知的技法形式和表现题材,比如陈文骥,比如俸正杰,比如蒋丛忆,他们的“新”“旧”之间都是让人觉得很讶异的反差很大的变化。而潘钺却是用“技术转型”来表现他从前惯常关注的对象和群体,用摄影手段将他所熟稔而得心应手的油画题材形式来进行“强调和提纯”——用自己的理解赋予了更多造像意义上的新语言,这个过程是一个先验的、试验的、体验的过程,也是一个组构和再造的过程,他是一个“新造像者”,也是一个“心”造像者。 古代画论中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可做其最好的注脚——从记录个人内心世界的视觉经历为切入点,扩而广之,辐射至对一个时代的全息式的记载——潘钺镜头下的“农民大头照系列”撷取农民出身的县级剧团戏曲演员、平日务农、节庆演出的腰鼓演员、秧歌演员,取完全正面的上半身摄影肖像,个个正襟危坐,一本正经,脸上所化的浓妆重彩夸张而显粗糙,零距离的直面接触夹带着具体而生动的现场信息感:演员们简陋戏服里面露出沾着污垢的西服衬衣的领子,演出服下的皮夹克内还打着领带的衬衣领口,有的女演员戏服破损,拿一颗别针别着领襟处,种种细节,五味杂陈;他们或苍凉、或木讷、或憨厚、或天真,耐人寻味。农民的生活现实历来是中国文化最浓重的底色,而潘氏镜头下的这种农民文娱演员的特殊的生活精神状态,呈现着这个特定时期社会大变转轨迹中的诸种特别景观。这是艺术家在深刻的洞察力的驱使下,从狭窄的独特性和个人化的创新强迫症愈演愈烈的歧路上聪明而理性的后退——在潘钺以往的绘画作品里,他更多地表现的是专业的戏曲演员,他们在舞台上的一招一式规范端严,而在他的摄影作品里,他关注和留意的是这些粗陋的、沾满尘土气息的、朴拙沧桑、自娱或娱人的农民演员,这种艺术视线的位移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潜在的变化,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的是艺术家内心深处人文情怀逐渐丰厚的滋生和扩展,作品虽然没有过多的背景和细节语言,但这种刻意的截取、筛选和过滤却更加意味深长,给人更深远的想象和沉思的空间。只有有心者,只有诚挚恳切的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细致比较他们的生活变化,方能更深刻地了解他们,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记录的具有民俗学及文化心理价值的人文图录——“境由心造”,潘钺用心在造像,用观念在造像,这种不动声色的述说让人默默地感动。 如果我们进一步扩开视线,会发现“从狭窄的独特性和个人化的创新强迫症愈演愈烈的歧路上聪明而理性的后退”,这一理念的转换源自我们的社会城市化的进程,这种向消费社会转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广告图像与影像在现实生活中的强势推进,这无法回避的现状令使敏锐的艺术家直觉地意识到构成现实环境的影像的压迫力量,并无形中催生一种以自己的影像语言与之对话、反制的表现冲动。这恰如潘钺自己所言:“我拍这些片子首先还是给中国人看的!具体的说是给生活在大城市、吃饱了饭、有些兴奋、容易健忘、经常愤怒、老把忘本二字挂嘴边上的国人看的。” 潘氏又云:“相信过去的时代也是有追星一族的,那时的明星就是戏曲演员,被称做‘戏子’,是属于下九流的行当。多种文学与影视作品揭示了那时的戏曲名角儿提供了并非单纯的演出服务。我现在做的不过是过去的人想做而不便做的工作,或许过去也有人做了但没有流传下来,即使在今天它似乎也应该被‘秘藏’起来。” 因此又催生了潘氏的另一类的摄影作品是“戏曲秘藏”系列——传统的戏曲剧目中的白娘子、小青、杜丽娘、杨贵妃、苏三等经典的旦角和青衣人物,披挂整齐的头面装饰——打底、敷粉、打出桃红面、眉黑刷眼刷眉、贴鬓角、吊眉、包头、或点翠或双光的头面,一应俱全,蹬上绣鞋,也有缨络飘飘,动作程式有板有眼,娇媚动人,却纷纷以裸体示人;苏三起解时,照例要带上长枷,但见那面长枷,晶光闪闪,华丽无比,戴在裸体跪地、头上点点翠翠的娇媚冷艳的弱女子身上,那种无以言说的撼动,惟观者自知。 另外,潘钺这两大类反差很大的作品系列可见潘钺意欲从广泛的文化层面介入,不惜放弃自己熟惯的油画语言,以摄影这个可以与社会生活发生多种对接和转换方式的媒介,对历史与记忆、性与欲望、身体与文化制度的关系、历史的戏仿、艺术样式的综合等各个层面的问题展述一种心与影、境与像的多重讨论。我们看到,从上世纪末开始,传播媒体的剧增、滚滚而来的商业大潮和诸多外来文化的全面渗入,为摄影家的生存带来一种新的机会,同时也根本性地改变了摄影家的生存方式。光怪陆离、铺天盖地的商业摄影渐欲迷人眼,而摄影的社会责任与现实关注功能却逐渐在淡化。就在摄影界中人面对这种变化显得有些无所适从时,美术界如潘钺这样的艺术家开始了他们的观念性的摄影探索,多变灵活的影像策略使得他们因此得以触及许多社会历史文化问题的内核,而这是表现方式单调空洞的纯粹摄影所无力把控的。他们的作品让我们发现,摄影艺术由此已经回归到人的本位,艺术家由原来被工具和技术掌控、向外境求索的反映论式的被动状态,转而向人的内心和观念寻求本源,对观念摄影中人而言,与当代生存方式休戚相关的当代“影像”概念是灵魂,摄影只是其观念的载体,他们着眼的是如何将摄影的社会纪事性特征作为元素整合到当代艺术的语汇、题材中,并进行新的语意转换。其实,不管什么样的影像方式,它们都会用直观的形式凝结社会生活形态的更迭,各种意识与观念的浓缩、解析和阐释,使得善于想象和变形的人类记忆,定格在这些凝固的影像之中。 (责任编辑:卓艺梵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