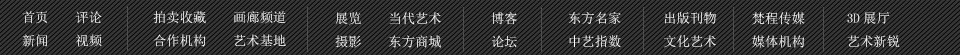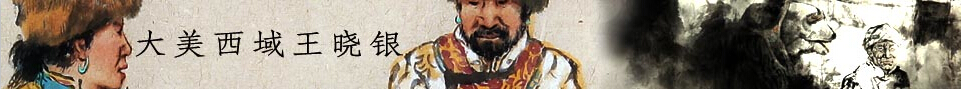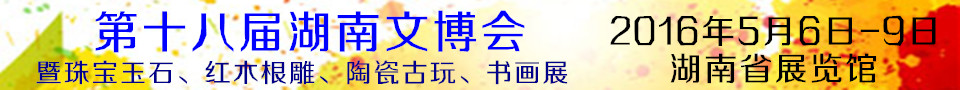上次的展览利用了带有现成品气质的广告灯箱架子作为了展览主体,而这次则完全靠展场具体环境,现场制造出来。在总结唐人个展的时候他曾对那些熬出二两血的创作经历总结出一个经验“从局部做起”。这个“从局部做起”在这次展览里面的确得到了很好的贯穿和执行。 从作品材料气质和情绪的把握上,现场横在展厅对角线上那道白铁皮,能在《好奇黄好奇之蓝》个展的那些广告架局部上面找到相近的气息。而那次展览里面黑色油脂从灯管滴下来的那种痕迹感,也被应用到这次展览里面。地面上从缝里看见那一滩黑色和那块透明的像未干的水迹就与此相关。 另外一个关于从局部做起是展览现场各个物体的造型,都是根据现场地面遗留下来的痕迹顺势而起,就势利用做成的,包括那些水泥墩,地面黑色油脂…… 甚至那片砸碎的灯管。都是被精心的安排到一个特定的痕迹范围之内。 整个展厅被密封,杜绝了一切外来光源。展览现场只靠作品自身发出的光线作为照明。在未干的水泥散发出的碱味里展场包裹在一种昏暗的冰凉气息里面。展厅里面作品相互呼应,错落在一起,不断的改变和引导观众的参观路线,观众只能身在作品之中并不能窥探到全部,每一作品之间的细部搭配就像绘画上的每一笔颜料相互协调又相互影响,细心观看都能找到很多精心埋下的感觉。此时所有材料的社会属性被材料本身形成的气质排斥在观看体验之外。所以在展厅里看到什么样的东西并不重要,材料属性、形状、质感被转化成情绪和气质,成为展场氛围,成为展览的主体。 从这个角度讲何岸在这个方向上越走越深,但是作为更宏观的创造而言,这些艺术创作中已经成熟的材料形成的情绪,氛围和展场对细节的处理何为一个可以停止的度? 细节与情绪在一起永远都是无穷无尽的深渊。那么这种“荷尔蒙”创作为谁而发,为何而发,是否需要考虑进去? 在去年个展之后的采访何岸自己说道:“当一个比较认真的艺术家很痛苦,至少我是这样的。我觉得搞艺术跟参禅一样,你每天都要面对一个自己的镜像,然后去想到底应该做什么。这很孤独,也很痛苦,你需要面对它。这是一个职业习惯,我认为必须树立这种习惯。有的时候真的可以产生这种幻觉。在唐人的那个展览的布展真的非常痛苦,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 做作品的时候感觉自己在分泌某种东西,感觉很疼,在最后一刻下了决心,但还是不确定……。” 在这次展览之后他也有过类似的感叹,再一次陷入到这样的焦虑里面,每次展览就像从一个焦虑跳进另一个焦虑。在焦虑里等待下一个焦虑,或许这个度,就来自他煎熬的程度? (责任编辑:卓艺梵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