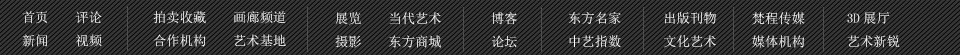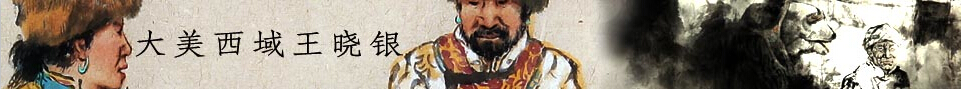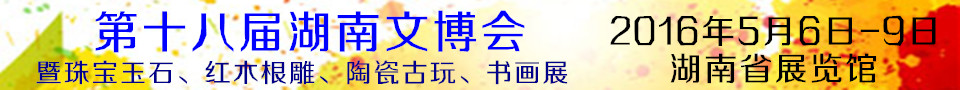最初,大多数的创作“问题”,都被抽象的归纳为了“拨乱反正”,在这一过程之中,如果不务虚言,人们所关注的,就自然应该是对艺术“本体”的回归。于是,我们领略到了在此之后各种艺术方式和艺术形式的全面“开放”。然而需要警觉的是,“形式”的层面,终究不可能解决全部的“问题”,在全力以赴的个人“图式”、“样式”、“风格”、以及“张力”的追求中,甚至在空洞的“观念”的张扬中,我们所失去的,都将是艺术创造精神的懈怠。如果具体一点地讲,不论是中国画领域的“笔墨”之争,还是前卫或观念艺术的甚嚣尘上,相当一部分的艺术实践,实际上都是在一种“小我”的情感方式中,抢占中国艺术史的当代“空白”,而并没有顾及多少“大我”的存在及其使命。 言必及“使命”,或许应该是周韶华先生那一代艺术家们维系艺术创作的共同理念。他们由一个特定的年代走出,又立足和面对一个新的时代景观,其中的曲折,不言而喻。从这个角度来看,周韶华先生先后提出的“全方位观照”、“横向移植”、“隔代遗传”等等,尽管并不是那种经过严密阐述而转化出的命题,但它们却真切地构成了一套实践艺术的原则、方式、态度和自我规范。 与此相印证,从八十年代起,《大河寻源》、《世纪风》、《梦溯仰韶》、直到目前的《汉唐雄风》,一系列的作品,以求“气”、求“大”、求“势”的直观印象,接踵而来。 使命感,往往和历史意识有关。在此,尽管我们不能粗略地对待历史的真实,然而也并非一定要拘泥学究式的阐释。视觉的艺术,终究汇集为感性的诉求。在周韶华先生的“观照”中、或经过这样的一些“观照”过程,历史不再抽象,而开始萌生语言的欲望,或者,通过图像的实验或引用而生动、具体起来。 近期的这一个《汉唐雄风》系列,由四个子序列组成,分别是:《汉唐雄魂》、《幻梦的净土》、《古往今来》、《天地人和》。前两列是主题性的丈二大幅,后两列呈现丰富的艺术图像史素材。由这些主题,可以充分地表明,在“寻源”以来的样式探索和创作观念的基础之上,周韶华先生是想继续“汲取艺术文化的复兴力量”。 在这批作品中,周韶华先生所贯注的精力,不仅仅是在于大幅面作品的制作劳动,另一方面,这也是对汉至唐代视觉文化遗产的全面检索和研习。最终,丰富而庞杂的视觉元素的假借和挪用,形成了这批以“汉唐”为主题的作品的美学标志,而一部分汉画拓片的拼贴,则直接在作品的形式与内容之间建立起视觉联想的语境。当然,汉唐的艺术,横跨了中古时代强悍的千年,显现着中原腹地的辉煌,也隐含着兵戎之气之中求静穆的气息,尽管它们并未延续为中华社会文化传统的全部。因此,在以“众生之相”为关怀的深沉和恢宏之中概括出来的历史追忆,构成了周韶华先生这一系列作品所张扬的一个宏大的主题,并通过“叙事性”的画面语言而展开。 系列作品之中,更能够显示其创作意义的,应当是那组《幻梦的净土》。 我始终觉得,在这样的一组作品中,周韶华先生依然是以一种求“变”的态度向自我挑战。就整体的印象与格局来看,这组作品在“图式”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新意”,相反,由于作品带有着某种回归绘画“语言”的倾向,尤其是那些“写实”形象的处理,倒使得这批新作与他惯常所熟练控制和驾驭的绘画形式产生了一些明显的疏离,并在画面的直观形态上显露出了一些“生”的感觉。 这种“生”的感觉,或许就是“生涩”,或者就是“生拙”。实际上,刻意地求“新”、求“奇”、求“生”,在艺术中都并不难得,难得的是“平中之奇”或“熟中之生”,令人辩证地目击视觉形态更深一层的生动和丰富。抽象的气势,被一致地认为是周韶华先生作品的基本性格,而写实的塑造,却始终不在他以往作品的有效控制之中,然而周韶华先生不回避这一点,在这批作品中一再露“生”,是值得我们揣摩再三的。回到画面本身来判断,“汉唐”的主题和内容,必然包含有各个具体的视觉元素,在展现其意义联想的过程中不可逾越,于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疏离感”的过程中勉力调整,“生”与“拙”,就反而被利用和转化为一种可贵的直觉,也构成为一种新鲜的精神趣味。 更具体地讲,这批作品是以一种纪念碑式的画面组合,应对了汉、唐期间最为典型的“庙堂气象”,而这种气象,恰恰随着唐、宋以后水墨表现性语言艺术的成熟而逐渐地缺失。有趣的是,这种艺术的成熟本身,是有赖于政教与庙堂的淡化,它使得“人本”的艺术,有可能超然于内敛和平淡的性格;然而,人本的“出世”与“逃逸”之极,也终究难免会少了许多恢宏的关怀与“载道”的精神。这真可谓艺术哲理辩证的两极。但总而言之,把握“庙堂”的气象,总归是一种正面的描述,是对“成教化,助人伦”的叙事性功能的回归,它们有如汉赋的铺陈,所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 《幻梦的净土》,确实是一种“直言”,而且几乎近于一种“直白”。作为一种视觉的语言,这一点反映为对现成图像的直接挪用,而挪用的结果,是恢复了这些图像的历史语境,并以它们原本就已经具备了的种种现世的表情,召唤着积极的入世精神,令人在维系群体的“天地人和”之中,感染上一层庄严的气氛。于是我们可以说,借助于经典图像的引导,或围绕着叙事性目标的画面因素组合,它们想要表达和实现的,是对那些图像内涵和意义的重新“观照”,以及对那些图像所隐含的精神气质的强调。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既然作品出之于一种图像的改造或再造,那么,人们也就会对这些图式自身的样式和质地提出品评的要求。就这一点来全面地衡量,从画像砖、石,陵墓雕塑,到石窟寺造像和满壁风动的“飞天”,整个汉、唐时期的视觉艺术经典,都被一一地唤醒,成为了整个《汉唐雄风》系列图像再造的“底本”,并划定了审美的范围。 严格地讲,“汉唐”是一种过于抽象的概念,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它们的并置,无法被对应或确认为一种统一的、或真实的制度和文化。但是,隐藏在“汉唐”这一概念背后的,确实是一种共通的精神与气质。作为一段被中国后期文明的转向所一度悬置了的历史,在其制度与规范的建构与推进之中,在其贵胄、士庶、以及平民性的冲突与变迁之中,在其异域文化交融和吸取的心态之中,在其日常宗教的沉醉与欢愉之中,也尤其在通过文献的阐释而残存的美学之中,包含着许多在我们今天值得遥望的信念。 “幻梦”所指向的,是一种自由的“想象”,也是一种永恒追求的假设,就其终极而言,当无可企及。 因此,对于目前的这一批《汉唐雄风》系列,我们可以套用这样的一句话来表达它们最为值得关注的一点:“并不在于它怎样忠实地解释过去,它的价值,在于怎样认真地儆戒未来”。也因此,它们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图像”的再造,而应该是图像“意义”的再造。 在我们目前的这个时代里,视觉艺术正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迅速地应对具体情景的变化,以求得艺术在当下的价值与功能,这一特征,按照周韶华先生在酝酿和创作《大河寻源》的时代就已经开始时兴的一种普遍说法,可以被称之为“文化的转型”。但是,具体艺术的方式关系到那些综合的判断,它们不仅仅涉及于图像的解读,也同样应当包含有思想史、当然包括艺术史的追问,而一切,终将在一个文化境遇的新的轮回中重建新的秩序。周韶华先生的这批新作,既然是于肇始于某种历史意识的自觉“观照”,那么它们所实现的理路,也就自然有待于历史的真切评判。 对于历史,对于历史的图像,我们难免会有一种“往昔已然逝去,重返不再可能”的感慨,但是,站在某种精神的角度,我们依然可以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说法,那就是:“遗忘抹去往昔,记忆改变往昔,”于是最为可怕的,恐怕就是“无知将我们全都淹没”。 沈 伟 (责任编辑:卓艺梵程) |